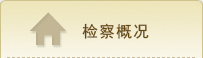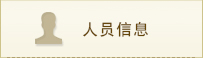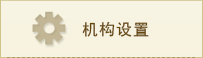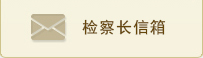当代中国的人民检察制度滥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检察制度是我国人民检察制度史上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新中国人民检察制度的雏形。我国现行的人民检察制度及其理论与陕甘宁边区人民检察制度最为密切,因而,对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检察制度进行研究,有助于呈现陕甘宁边区人民检察制度的宽阔视角,同时为完善当代中国的人民检察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本土资源”。
一、引言:重拾历史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9月6日,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陕甘宁边区的建制被撤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存在时间为1937年9月至1950年1月,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检察制度的积极探索。在检察制度建设上,“民主政权为保障抗日民主制度及边区人民的合法利益,在建立审判制度的同时,即建立了相同性质的检察制度。”#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历经风雨、探索前进。
二、历经风雨:陕甘宁边区检察机构的设置
就陕甘宁边区检察机构的设置而言,出现过三种机构设置模式:一是检察官配置制;二是审检合署制;三是审检分立制。
(一)检察官配置制
“所谓检察官配置制,是指国家并不设立自成体系的检察机关,而只是在各级审判机关内部配置一定数目的检察官,专门行使检察权。”$理论界通常将此种模式亦归结为审检合署制的一种形式,但笔者认为在审检合署制中,虽然检察机关附设于审判机关内,但仍然设有检察机关,有自己的组织体系;而在检察官配置制中,只是在审判机关内配置检察官,并没有自己的检察组织体系,因而,两者是有区别的。
1937年5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以下简称《组织纲要》),该纲要第八条规定:“边区政府设秘书处、建设厅、农工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保安司令、法院、审计处等”。1937年7月12日,根据《组织纲要》的规定,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正式成立,谢觉哉任院长,法院内配置有检察员。“1937年8月至1939年3月,在边区高等法院内部设有检察员(1937年8月至1938年12月,检察员为徐时奎,又写作徐世奎),对案件先行审查,然后提起诉讼。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检察员为刘福明。……这一时期,有些县设立有专门的检察员,有些县审判员兼任检察职务。”%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决定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设置检察处。由此可知,在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之后的1937年9月至1939年1月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检察机构的设置,采用的是在法院内配置检察员模式,即检察官配置制。
(二)审检合署制
“所谓审检合署制,就是将各级检察机关设置于相应审判机关内部的模式。” &“陕甘宁边区检察制度的特点是基本上实行审检合署,在法院内设检察处,配备检察人员。” '即将检察机关设在审判机关之内,而不单独设立检察机关。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决定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设置检察处,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以下简称《组织条例》),规定高等法院设置检察处、民事法庭、刑事法庭、书记室、看守所、总务科等部门,《组织条例》第12条规定:“高等法院检察处,设检察长及检察员,独立行使其检察职权。” 1941年3月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正式成立,李木庵担任检察长,下设检察员和书记员,各县设检察员1人,检察行政事务仍由高等法院管理。到1942年1月,边区实施精兵简政,检察处和各县检察员一并裁撤,检察机关的职权,凡属于汉奸、盗匪、间谍、暗害分子的政治性案件的侦查和公诉,由保安机关或公安机关行使,一般刑事案件由司法机关代行其职权。此后,屡有关于恢复设置检察机关的建议,由于战时环境和干部的极度缺乏,未能实现。(
1946年5月5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会决定在边区高等法院设置检察处(恢复设置,仍为审检合署),设检察长1人、检察员2人、主任书记员1人、书记员2人,任命马定邦同志为检察长。1946年10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改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从上述叙述可知,从1939年1月决定设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到1942年1月检察处和各县检察员一并裁撤,这一时期检察机构设置模式是审检合署制,1946年5月5日恢复设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到1946年10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改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这一时期检察处还是设置在审判机关内,并没有单独设置出来,检察机构设置模式仍然是审检合署制。
(三)审检分立制
所谓审检分立制,是指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在机构设置上各自独立,自成体系。1946年10月19日,根据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关于健全检察制度的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改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各分区设高等检察分处,各县(市)设检察处。边区高等检察处检察长仍由马定邦担任,并任命刘临福、折永年等为检察员。)这一次建立的检察机关从配置于法院的体制中独立出来,直接受边区政府领导,而不再受高等法院领导,确立了审检分立的检察体制。
1946年11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明确了各级检察机关之职权、组织及领导关系。各级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是:边区高等检察处设检察长1人、检察员2人、主任书记员1人、书记员2人;各分区设高等检察分处,设检察员1人、书记员1人;各县(市)设检察处,设检察员1人、书记员1人;小县则设检察员1人。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是:高等检察处受边区政府的领导,独立行使检察权;各高等检察分处及县(市)检察处均直接接受高等检察长的领导。*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犯边区,检察人员因参加军事行动而停止检察工作,检察机关实际上无形取消了。直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被撤销,再没有建立检察机关。这是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在陕甘宁边区第三次建立检察机关,这一次建立的检察机关在检察体制上实行审检分立制,彻底改变了以前“审检合署”或“配置制”的做法,首次确立了审检分立的检察体制,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前首次建立的独立的检察机关组织系统,标志着人民检察制度开始向独立体系迈进。+在推进人民检察体制建设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标志着陕甘宁边区的检察制度已经开始走向成熟。
三、探索前进:陕甘宁边区检察机构的职权配置
如上所述,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基本上实行的是审检合署制,在法院内设检察处,配置检察员。尽管在检察机构设置上,大部分时期是在法院内设检察处,配备检察人员,检察机关并未从法院机关独立出来,自成体系,但在检察职权配置上,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其检察职权,当然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检察机关的职权只是“半权”,检察机关的独立只是“半独立”。
(一)检察“半权”与“半独立”
1.大部分时期没有单独设立检察机关,只是法院的一个部门。与当代检察机构设置情况相比,陕甘宁边区检察机构设置模式基本上实行的是审检合署制,在法院内设检察处,配置检察人员,而没有单独设立检察机关。1939年4月颁布的《组织条例》和1946年10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暂行检察条例》(以下简称《检察条例》)均规定了审检合署的检察机构设置模式。《组织条例》第7条规定“高等法院设置下列部门:(一)检察处”。《检察条例》第2条规定:“高等法院配置高等检察处,设检察长一人,检察员若干人,书记员若干人,视事之繁简定之。”第3条到第5条规定了高等法院分庭和地方法院设检察员和书记员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检察立法并没有规定设置独立的检察机关,而是将其作为法院的一个部门。在此情况下,检察处内部就没有再设立机构,直接由检察员和书记员组成。同时《组织条例》规定,在高等法院设置检察处,设检察长及检察员,书记员统一设在法院书记室,根据需要随从检察员执行职务,检察处行政事务由高等法院管理。
2.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其检察职权。1939年4月颁布的《组织条例》第12条规定:“高等法院检察处,设检察长及检察员,独立行使其检察职权。”与高等法院的管辖不同,《组织条例》规定“高等法院受中央最高法院之管辖”,这说明边区高等法院和中央最高法院具有名义上的管辖关系,而高等法院检察处与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之间没有任何领导和管辖关系。同时对于检察人员内部的领导关系,《检察条例》规定:“高等检察长领导全边区各级检察员,高等分庭检察员领导所属各县检察员,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员领导该院检察员。”1946年10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健全检察制度的有关决定》(以下简称《有关决定》)进一步明确,高等检察处受边区政府之领导,独立行使职权。各高等检察处及县(市)检察处均直接受高等检察长之领导。这说明各级检察员不受地方领导,在检察人员内部之间是垂直领导关系。,从上述分析可知,检察权只是“半权”,检察机关也只能是“半独立”。
(二)监督审判活动与监督判决之执行
我国现行《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2012年刑诉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和法律的功能定位与陕甘宁边区检察立法的优良传统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陕甘宁检察立法没有对检察机关的性质进行定位,但在检察立法中关于检察职权的规定方面,体现了浓厚的法律监督色彩。-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除承担一般监督的职能,即对违反宪法、行政法及政策之行为进行监督外,还承担着对审判机关行使职权的活动进行监督和监督判决执行的职能,具体来说:
1.监督审判活动。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最直接的方式是提起公诉、出席法庭。陕甘宁边区的检察立法对此作出了规定。1939年4月颁布的《组织条例》规定检察员职权共分8项,其中第4项为“提起公诉并撰拟公诉书”。1946年10月颁布的《检察条例》将检察职权分为10项,其中第6项规定为“提起公诉或提付行政处分”。而在检察实践中,如“黄克功案”.较为详细地呈现了检察机关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职能的实现情况。检察机关在“黄克功案”中起草完成了公诉书。1937年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抗大政治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法院检察官徐时奎作为法院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陈述意见。“黄克功案”充分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出席法庭”的检察职权的实现情况。
2.监督判决之执行。监督判决之执行,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1937年2月22日,陕甘宁边区颁布的《中央司法部训令第二号》第2条规定:“关于刑事案件的执行,应有各级国家检察员指挥,死刑的执行,必须由国家检察员呈送卷判及证物件来部审核,经本部核准后方可执行。”1939年4月颁布的《组织条例》规定检察员职权共分为8项,其中第7项为“监督判决之执行”。这里的监督判决之执行包括监督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之执行。1946年10月颁布的《检察条例》将检察职权分为10项,其中第9项为“指挥刑事判决之执行”。这些规定就是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监督判决之执行的法律渊源。
四、本土资源:陕甘宁边区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经验
通过前文对陕甘宁边区检察机构的设置、职权的配置分析可知,陕甘宁边区时期人民检察制度伴随着革命斗争的起伏跌宕,机构设置、职权配置甚至地位和作用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反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怎样结合边区实际情况设立检察机关,确立怎样的检察制度,有一个实践探索和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陕甘宁边区人民检察制度在组织机构和业务建设上都很不健全,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检察制度不仅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创建准备了条件,对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提供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具有熠熠生辉的当代意义。
(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我国人民检察制度的政治优势
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成立,这是人民检察制度的光辉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政权实行“一元化”领导下,从成立检察机关开始,就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优良传统。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也是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所谓‘一元化’体制,即一切由党领导的体制。一是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党的组织领导一切。二是在中共党内的上下级关系上,‘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第一点来看,司法机关与各行政机关、民间团体一样,都是党领导下的组织。”/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法院内配置有检察员。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决定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设置检察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拥有审判、检察、司法行政三种职能,同时受边区参议会之监督,边区政府之领导。
陕甘宁边区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司法工作中的体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时各级司法机关处理刑民案件的依据,就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所颁布的带有法律性质的纲领、决议、决定、布告和法令,检察工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实、严格地贯彻执行依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这就是说,边区的司法建设和实践包括人民检察制度建设及检察实践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着、发展着。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工作中,党直接介入司法的过程,过问具体案件,甚至直接参与审判决策,边区主席、副主席的意见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起决定作用,在一些重大案件中,司法机关更是要向中央请示汇报。0如1937年10月发生的“黄克功案”,负责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雷经天写信向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回信说“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黄克功最终被判处死刑。“翻阅边区高等法院的案卷,无论刑事、民事,经常可见到各级党政军负责人的意见、批答或批示,甚至不乏司法人员的主动请示、汇报。”1从上述分析可见,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检察制度建设和实践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检察机关的优良传统,是我国人民检察制度的根本特征和政治优势。
(二)保留并完善检察机关,是我国人民检察制度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的发展历史来看,边区检察机关出现过几次废立。1942年1月,边区实施“精兵简政”,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和各县检察员一并被裁撤。此后,屡有关于恢复设置检察机关的建议,由于战时环境和干部的极度缺乏,未能实现。直到1946年5月5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决定恢复设置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1946年10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改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但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司法干部有的转入部队,有的去搞战勤工作,检察机关实际上无形取消,直到陕甘宁政府撤销,再没有建立检察机关。
1942年1月边区政府裁撤检察处和各县检察员,引起了极大的纷争。以李木庵、鲁佛民、朱婴为代表的专业司法人员主张保留并完善检察机关。他们主要是从历史、法理、司法实践等角度论述检察机关存在的必要性。如朱婴在写于1942年1月的《论检察制度》一文中,主要从这是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在具体职能上,检察机关也是必需的;检察机关的设立还可以使审判工作专一公正;检察机关还能提高司法机关的威信等方面,论述了检察机关的必需性。而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为代表的主张设置检察机关已无必要,他们主要是鉴于边区的政治、司法、社会背景等原因,主张边区不需要检察机关。2从上述分析可知,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时存时废,且1942年边区政府裁撤检察处和各县检察员,引起了极大的纷争。时存时废的边区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建设及检察机关存废之争的讨论影响深远,检察机关在陕甘宁边区设置、裁撤、恢复设置、无形取消的反复,这也是设置检察机关必经的探索过程,检察机关存废之争的讨论厘清了许多模糊的认识,使后人对检察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当今时代检察制度的完善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检察体制从审检合署制走向审检分立制,体现了我国人民检察制度的发展方向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陕甘宁边区政府有三次建立检察机构。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决定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设置检察处,1946年5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决定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恢复设置检察处,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改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各分区设高等检察分处,各县市设检察处。前二次建立的检察机构基本上实行的是审检合署制,在法院内设检察处,配置检察人员。1946年10月第三次建立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较以前有很大不同,“一是在检察体制上实行审检分立制,彻底改变了以前‘审检合署’或‘配置制’的做法;二是在领导关系上,受边区政府的领导,而不再受高等法院领导。”3可见,1946年10月建立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把检察处从配置于法院的体制中分离出来,直接隶属于边区政府,从而确立了审检分立的检察体制。同时1946年10月颁布的《检察条例》第四章规定:“在全国和平统一未实行前,高等检察长由边区政府领导之。”相应的边区政府命令则明确规定:“领导关系:一,高等检察处受边区政府之领导,独立行使职权。”由此可见,《检察条例》和边区政府的命令明确了审检分立的检察体制。
其实,早在1941年11月鲁佛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边区司法的几点意见》的文章,提出实行检察独立制度,认为检察制度是经过了血的教训而演变过来的,18世纪法国革命成立后,便设立检察制度,与审判部分分开,这是适合革命的、民主的需要而设立的,借以防止审判机关的武断专行。1942年1月朱婴在其《论检察制度》一文中,论述了检察独立的必然性及其原因,认为检察机关断不是局促在一个法院内所能担负起来的,一定要独立对外,一定要独立行使其职权。即检察制度的独立性是其本身所具有的自然规律。41942年6月,李木庵取代雷经天出任高等法院代院长,在他的主持下,边区司法系统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改革,其中检察独立是重要内容之一,主张检察机关从法院机关独立出来,自成体系。上述以李木庵、鲁佛民、朱婴为代表的专业司法人员的“闹独立性”,尽管由于与当时边区实际和边区人民的需要有较大差距,实际上是失败了,但是李木庵等人关于把检察机关从法院机关独立出来,自成体系的主张,体现了人民检察制度的发展方向,对建国后的检察制度的确立不无影响,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1946年10月颁布的主要体现了以李木庵为代表的“独立派”的主张的《检察条例》中关于审检分立的检察体制的规定,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一府两院”的渊源之一。5
(四)检察权的配置体现浓厚的法律监督色彩,反映了我国人民检察制度中检察权的基本属性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虽然陕甘宁边区检察立法文本中没有出现“法律监督”一词,但是其内容却蕴涵在“检察”一词中,从1946年10月颁布的《检察条例》关于检察权的内容和范围的规定来看,陕甘宁人民检察制度中的检察权已经体现出了较多的“法律监督”色彩。6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除承担一般监督的职能,即对违反宪法、行政法、政策行为之监督之外,还承担对审判机关行使职权活动实行监督和监督判决之执行的职能。1939年4月颁布的《组织条例》规定检察员职权共为8项,其中第4项“提起公诉,撰拟公诉书”;第5项“协助担当自诉”;第6项“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第7项“监督判决之执行”。1946年10月颁布的《检察条例》将检察职权分为10项,其中第2项“关于宪法内所定人民权利义务,经济财政及选举等之违反事项”;第3项“关于行政法规内所定之惩罚事项”;第4项“关于一般民事案件内之有关公益事项,如土地租佃、公营事业、婚姻等”;第6项“提起公诉或提付行政处分”;第7项“协助自诉”;第9项“指挥刑事判决之执行”。与《组织条例》规定的检察职权范围相比,《检察条例》增加了监督权的内容,包括了一般监督的内容,如对违反宪法、行政法行为之监督。1946年10月颁布的《有关决定》规定了各级检察机关之职责,包括:1.关于一切破坏民主政权、侵犯人民权利的违法行为的检举;2.关于各级公务人员触犯行政法规的检举;3.关于违反政策之事项(如违反租佃条例)的检举。从《有关决定》规定的内容来看,更加强调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并赋予了其移送行政处分的权力。总之,从上述陕甘宁边区检察立法对检察权的规定变化来看,一方面,检察职权呈扩张趋势;另一方面,呈现了越来越突出的监督权的色彩。7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检察制度继承和发扬了检察权的基本属性是法律监督权这一法律传统,在现行《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和法律的功能定位与陕甘宁边区检察立法的优良传统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陕甘宁边区检察立法规定检察职权具有法律监督的功能,反映了我国人民检察制度中检察权的基本属性,体现了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为新中国成立后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和法律的功能定位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五、结语:薪火相传
缅怀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当今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提出“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要求。而陕甘宁边区在人民检察制度建设和实践的探索中作出了大胆尝试,它所形成的一些检察理念和做法,如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检察独立制度、检察体制由审检合署走向审检分立、检察权的配置体现浓厚的法律监督色彩等,这些都为思考当代中国人民检察制度建设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相对于西方现代检察制度来说,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本土资源”。对于思考当今中国人民检察制度建设问题仍不无启迪,值得借鉴,也是今天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的基本原则,应该薪火相传。
" 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 张培田、张华:《近现代中国审判检察制度的演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 桂万先:《近代中国审检关系探析》,《学术研究》2007年第6期。
% 巩富文主编:《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1页。
& 桂万先:《近代中国审检关系探析》,《学术研究》2007年第6期。
' 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 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 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 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 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 参见巩富文主编:《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 参见巩富文主编:《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页。
. 1937年8月间,黄克功与投奔延安不久的进步学生、年仅16岁的刘茜发生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但因两人婚姻、家庭观念的差异,刘茜渐渐疏远、继而拒绝了黄克功。黄克功仍穷追不舍,终因逼婚未遂而于10月5日傍晚在延河畔连开两枪,残忍地杀害了刘茜。参见刘全娥:《黄克功案的法律意义》,《法律史评议》(第7卷),第266页。
/ 胡永恒:《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司法“半权”—以陕甘宁边区治理为例》,《文化纵横》2015年第2期。
0 参见高运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实践—以审判工作为中心的研究》,湘潭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第11页。
1 胡永恒:《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司法“半权”—以陕甘宁边区治理为例》,《文化纵横》2015年第2期。
2 参见巩富文主编:《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150页。
3 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4 参见巩富文主编:《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152页。
5 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6 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7 参见巩富文主编:《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页。